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陕工网(029-87344649)
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陕工网(029-87344649)第五建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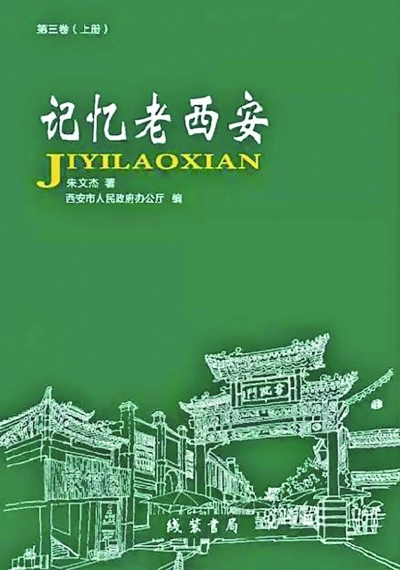
他本无心书写历史,却给历史加了一个注解。这是我读朱文杰先生《记忆老西安》系列之书的第一印象。
早在2019年收到朱文杰先生赠我他的第一套《记忆老西安》时,我翻看目录,捧书的手就开始颤抖。古籍浩如烟海,而《记忆老西安》毫无疑问是我所读其中最璀璨的作品之一。它犹如时间的长河记载着千百年来的西安发展史,无论是政治风云、时代更替、经济变迁、文化思想的交锋、城市面貌的变化等,朱文杰先生都以独特的纪传写真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立体画卷,巧妙地将时代人物、王朝兴衰、日月更新等串联成守护历史文脉、贯穿华夏文明的宏伟篇章。
《记忆老西安》这部厚重的城市传记,可以说是在时光褶皱中打捞一座城市的灵魂,目前此书已出版了五卷本(上下集共十本)近三百万字的体量,在当代城市文化志中堪称异数。这部书最动人的特质,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志的编年框架,将历史叙事溶解在街道巷陌的肌理之中。如四府街的青石板、湘子庙街的槐树影、北院门飘散的羊肉泡馍香气等,这些鲜活的细节构成了一部可触可感的城市生命史。作者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精神,在西安城的历史褶皱里,打捞出无数即将湮灭的城市基因,相较于那些档案的宏大叙事,该书呈现出独特的“微观史学”价值。它通过上千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,让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市井烟火、未被文献记录的民间技艺,在《记忆老西安》中获得了永生。这种以个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,使本书成为西安城市记忆库中不可或缺的“民间底本”。当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与城中村的叫卖声在纸页间交响,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城市的历史年轮,更是文明传承的隐秘路径。
当看到书中记载了我在《长安》杂志社与路遥初相识的经历时,我的眼泪竟不受自控地溢了出来。看着照片,这个在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的陕北汉子,可以说铸造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碑。书中记录的细碎场景,恰似散落的时间琥珀,让曾经模糊的记忆重新泛起温润的光泽。还有青年路、北大街、西安人民剧院、报话大楼、和平电影院,承载着我的整个青春与光谱,因为我家就在青年路的团市委大院,报话大楼是我真正进入西安工作的第一站。朱先生笔下那个爬满紫藤的西安人民剧院,正是我们这群“电信机关青年”8小时之外的秘密基地。书中提及的公共水房、砖砌花坛、褪色的宣传栏,像被施了魔法般在眼前复活。当读到青年路消失的印刷厂时,鼻腔里似乎又涌入了油印试卷与线装书混杂的独特气息。这些文字不仅唤醒了个体记忆,更在集体无意识中打捞起整代人的精神胎记。
我与朱文杰先生可谓笔墨相照的知音之交,我们两个开始都是写诗歌的,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“在地性”写作的纯粹。他拒绝文化猎奇的写作姿态,以考古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,在寻常巷陌中勘探文明矿脉。每当夜深人静翻阅先生赠书,总能在字里行间听见长安城的脉搏跳动,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和坚持向朱文杰老师学习写作笔法的原因。就《记忆老西安》而言,在学术维度上,它开创了城市记忆书写的新范式。巧妙融合了口述史、物质文化研究与空间叙事学,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。书中对“西仓档子”市集的人类学观察,对回坊建筑谱系的类型学分析,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,打破了地方志写作的固有窠臼。可以说该书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其“抢救性记录”的紧迫意识。书中收录的上百份老字号账本、近千张消失店铺的照片、超百位老匠人的影像记录,构成了一座立体的城市基因库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档案,实则是解码城市文化DNA的关键。站在永宁门的城墙上,眺望古今长安,朱文杰先生用笔墨为当代也为后人铸造了一座记忆的方舟。当电子导航覆盖了城市肌理,当连锁商铺吞噬了市井个性,这部著作的存在本身,就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。它告诉我们:真正的城市灵魂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,而在百姓晨昏的炊烟中,在孩童嬉戏的巷弄里,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深处。这或许就是《记忆老西安》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——守护记忆,就是守护文明的火种。
责任编辑:白子璐

关注公众号,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